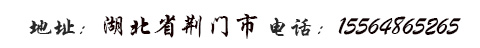水毛茛瘴雨蛮烟
|
我不知道为什么重庆的天空总是紫色的。过度深重的紫色,泛红诡异的紫色,喘不过气的紫色,从张牙舞爪的黄葛树枝叶间冒出一点形状,凝重地涂抹些许颜色。天空难找,仅在楼间几方几方的勉强存在,倒映着地面暧昧不明的光,红、绿、白,冷暖都分不清的样子。楼丛比树丛茂密,从坡上谷里长出来,不分黑白一股脑儿地长,新旧交杂,没有廉耻观地长。 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很容易失去重量感。普罗泰戈拉不无自傲地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呼一吸一挥手一迈步决定宇宙的形状,植根于经验。但如此经验在此却是不适用的,高低起伏曲折回环的底界面迫使每个角度都充塞了浓度过高的填充物,像空气里的水汽长期饱和,仅仅在视觉上便填满了眼眶,不容许想象力进一步飞驰。远远看去是娇小的巧克力排块一样的房子却是数不清层数的,每一个窄窄的小格就是一户人家,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么旧那么破那么高,邻挨着邻房挨着房密密麻麻声势浩大,压缩成平面却只能坍塌进一个像素的狭小空间里,再没了声音。源自惊奇的影像。与经验断联的结果便是感受力的下滑,地景成了纯粹视觉的形象,观看成了唯一的体验方式,身处其中与隔着屏幕只有转动脖颈的差别——只剩下密集、平滑、难以估量的城市图象,人类销声匿迹。 同样奇观化的还有街景。嘈杂的红,油滑的白,穿过榕树藤蔓坠落到灰褐色砖面上,砸下一阵麻椒螺蛳粉的气味,沐浴同样鲜红翠绿的人群。奇形怪状。与主流文化相去甚远,便成了一个恣意妄为的空间,常见扛着半人高垃圾袋的劳工与身着不辨真假DiorGucci的青年女郎擦肩而过,毛发旺盛的大狗和穿着清凉的小孩在同一片街道上相互追逐。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人与动物之间也没有太大的距离。很难说这究竟是好是坏。没有太多自诩高雅的文饰之心,便没有了折叠城市里一层见不到另一层的情形,但即便分享同一片天空,频繁的出现也只确认了区隔的自然而然与无可争议。他们仍是景观,纵使我心生怜悯。 在重庆的一年里我成为了无可非议的便利店沙拉品鉴大师,对蔬菜的二十种口感如数家珍,却依旧不食辣味。离开家乡才反反复复想起杭州的好,平湖秋月水杉树林,平和的,文雅谦逊。在这般狂乱而张扬不羁的世界里,能被我吞咽的只有表象,声音、气味、形态的形态、错杂的空间,而它们各自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从属于哪一种类型,我却是不知道的。缺少坐标的文化荒漠,比西伯利亚复杂得多得多,大量外来人口导致江湖味浓重,没有丝毫古典主义的影子。同样的原因让这片飞地对外来思想来者不拒,可以说是机缘巧合或是命中注定地成了革命熔炉,复杂、险恶、不稳定、便于隐匿。身处其中便是一连串接着一连串的惊奇,空气里涌动的信息像从不停止的重庆话一样冲向我、洗刷我、搅乱我,却再也找不到小布尔乔亚们努力维持的平静。许多时候饱和且浓稠的低纬度乔木仍会在黑夜里重复地念叨“无所不可”,但在瓦数过高的照明灯下我流连于地面的影子却也还并未改变。 正好是午饭时间,花椒歌舞升平,好呛。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aodichongbing.com/mxmdcb/6834.html
- 上一篇文章: 有毒植物丨毛茛
- 下一篇文章: 甲硝唑片说明书的适应症你真的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