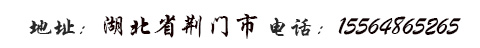伤寒论口渴辨治及其在临床中的运用
|
口渴症状在临床各种疾病中较为常见,由于其易被察觉和诊断中简便易行,往往成为我们诊疗过程中一个不应忽视的内容。对口渴症状的正确把握有助于我们正确的辨证论治和配伍用药。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伤寒论》有关口渴的诊治,阐述出现口渴症状的病机和其用药规律,为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提供参考。 在《伤寒论》中对“口渴”的称谓有很多,如“意欲饮水、渴、渴引浆水、饮水、燥渴、口燥咽干、欲饮水数升、舌上燥而渴、大渴、大烦渴、消渴”等等,都对口渴的轻重程度及其表现的不同性质特点作了描述。《伤寒论》中与口渴有关的条文多达50余条,其中以口渴为主症的条文就有33条,约占全书条文的十分之一,可见口渴在疾病过程中是比较常见的症状。现就我个人的一点认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阐述,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伤寒论》有关口渴的主要中医病机 《伤寒论》中涉及治疗口渴的方药有10余首,另有针刺法1种。从“以方测证”的角度我们可以概括出四大主要病机,一是燥热伤津的口渴,如白虎加人参汤证;二是“蓄水”津液不布而至的口渴,如五苓散证;三是水热互结而至的口渴,如猪苓汤证;四是寒性疾病阳复向愈的口渴。 1、燥热伤津的口渴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卷二》渴第二十九[1]中云:“渴者,里有热也”。《伤寒论》26条有“大烦渴不解”,在条有“舌上燥而烦,欲饮水数升”,在条有“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等,都强调了热盛伤津耗气的时候是大渴,方用白虎加人参汤。其中白虎汤清其热,人参甘寒以益其气,解决大烦渴的问题。与之对应而值得一提的是,白虎汤证在《伤寒论》条、条、条中没有言及口渴,但我们从以方测证的角度不难看出白虎汤证应该口渴。这种口渴可能是热初始,未损津耗气之甚时的一般口渴。 2、“蓄水”引起的口渴蓄水引起的口渴也就是机体水液代谢障碍出现的口渴。《素问·经脉别论篇》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此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医论及的水液代谢实际上涉及到肺、脾、肾、膀胱以及三焦等各部位,其中那一个环节出现障碍或气化不利,都会引起“蓄水”出现口渴和小便不利等症状。《伤寒论》条“病在阳,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潠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弥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与五苓散主之”。此条所表述的是表病当汗,反用冷水浇灌,使皮肤郁闭,肺气受阻,津液不能输布,轻者只感“意欲饮水”并不太渴,用文蛤散治疗即可;如果肺气受阻较重,不能宣发津液而口渴明显时,就要用五苓散治疗了。71条“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清·张锡驹《伤寒论直解》云:“小便不利消渴者,乃脾不转输,水津不布而消渴,故用五苓散以解之”。认为“水逆”是由于脾不转输而导致。条“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痞不解”当是中焦水湿气化不利。 3、水热互结的口渴水热互结的口渴既有热伤津液又有水湿不布,《伤寒论》条“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条“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一是阳明内热损伤了肾阴,阴虚更生内热;二是下焦气化不利而水湿停滞。阴虚内热与下焦水湿停滞相合形成较复杂的病机,因此出现的症状也比较多。小便不利是水湿互结造成;渴而口燥烦是阴虚内热,同时也有水津不布的因素;水湿偏渗大肠则为下利;阴虚火旺气易于上逆,水热上犯肺则咳;犯胃则呕;上扰则不得眠。故用猪苓汤清热养阴利湿治之。 4、阳复向愈时的口渴在伤寒病过程中,口渴症状未必都表示病态,也可以是疾病向愈的一个征象。此类口渴多发生于寒性疾病,其病原本无渴,经治疗后出现口渴,常常表示阴寒之邪去而阳热之气恢复。故口渴这时可做为疾病向愈的征象,如《伤寒论》41条:“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此条之症因阴寒内阻,而口淡不渴,服温阳散饮之小青龙汤,阳气来复,寒气随去,故口渴。 二、《伤寒论》中各种口渴的证治 清·陶憺庵《伤寒源流》卷三·渴总论[2]中对口渴的治疗主张“然阳经之渴,须分标病本病,以行和表渗湿润燥攻实之殊;阴经之渴,须分本经传经,以尽清热与水顺下温经之变。至于传经尽时,病欲饮水,为自愈之候,但未可极意恣饮。”为我们正确领会《伤寒论》对口渴的证治有很大的帮助。 《伤寒论》各篇都有对口渴的证治,其中以太阳病篇中篇和下篇及阳明病篇的条文较多。白虎加人参汤证口渴、文蛤散证口渴、茯苓汤证口渴、猪苓汤证口渴、小青龙汤证口渴如前所述,下面将其余方证的口渴做一简述: 1、大陷胸汤证口渴《伤寒论》、、、条论述了大陷胸汤的病证和治疗。在条中云:“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描述了其实热结胸证特点,是因太阳病表未解医反下之,邪热乘虚内陷与水饮实邪互结于上焦,气机阻滞,津液不得上布而致“舌上燥而渴”,属水热互结的口渴。用大陷胸汤泻下热结“得快利而止后服。” 2、茵陈蒿汤证口渴《伤寒论》条“阳明病......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身热发黄属湿热证,一般不口渴,但此条却有口渴欲饮浆水,这是热邪郁闭于内,水湿停滞而不能化生津液,属湿热互结的口渴。用茵陈蒿汤清热利湿退黄,使湿热分消,三焦通利而湿热祛黄退。 3、小柴胡汤证口渴《伤寒论》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或渴......小柴胡汤主之”。少阳病本没有口渴,有口渴也属于或然症。只有少阳之热内涉阳明的时候,津液受损才出现口渴,此属有热伤津的口渴。97条“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进一步论证了此口渴为热及阳明伤津而引起。以小柴胡汤和解退热,津复渴止,不已,以阳明法治之即可。 4、柴胡桂枝干姜汤证口渴《伤寒论》条“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柴胡证一般胸胁满而不结,又见渴而不呕,小便不利,知非纯属少阳证,有兼证水饮内停存在。少阳分司胆与三焦,当胆火内郁,疏泄失常时,则三焦决渎失职,气机阻滞,以致水饮停蓄不行而小便不利,气不化津而口渴。此属水饮不化的口渴。以柴胡桂枝干姜汤一则和解少阳枢机之邪,一则助气化而生津液。 5、白头翁汤证口渴《伤寒论》条“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此条是对条“热利,下重”的补充,是湿热下利而邪热偏重引起的口渴。以白头翁汤清热燥湿,凉血止利。 6、刺期门穴的口渴《伤寒论》条“伤寒发热,啬穑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瞒,自汗出,小便不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肺主皮毛,肺受肝木所制,失去肃降功能,不能通调水道而小便不利,气不化津,津液不能上承而渴欲饮水。刺期门穴,泻肝救肺,恢复肺气的功能。此亦属于水饮不化的口渴。 7、大承气汤证口渴《伤寒论》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条“少阴病,自利清水······口燥咽干者,可下之,宜大承气汤”。论述了少阴热邪亢盛。津伤邪结的辨证与治疗。亦属热伤津液的口渴,以大承气汤急下存阴。 三、《伤寒论》口渴证治浅析 口渴在《伤寒论》中可作为很多疾病的辨治要点和论治依据,也可作为据此判断疾病的预后转归。 1、作为疾病的辨证要点和论治依据《伤寒论》中对证情相似的复杂疾病常能抓住重点而施以不同治法,其中不少是以辨渴作为依据。如条“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恼,舌上苔者,栀子豉汤主之;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清·柯韵伯注曰:“栀子豉汤所不及者,白虎汤继之,白虎汤不及,猪苓汤继之,此阳明起手三法”。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下后热扰胸膈,舌上白苔,口渴不明显者,宜栀子豉汤清宣胸膈郁热;阳明热盛,舌燥口渴者,宜白虎加人参汤清热生津;津伤而水热互结,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宜猪苓汤养阴清热。此条文是根据口渴的程度和其他兼证辨别阳明经证误下后的几种变证。 又73条“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明确提出以渴与不渴作为两个方证的鉴别和论治依据。二方皆为水气而设,五苓散证中口渴与脉浮发热、小便不利并见,为太阳之邪循经入腑、热与水结、气化不利所致,故治以化气行水;茯苓甘草汤证为胃阳不足,水饮停于胃中,热虽入里,未与水结,故治以温胃化饮。在条(引条文如前)中言病在太阳误治后出现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等,这与“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的五苓散证很难辨别,因此用“反不渴”突出了辨证的要点和论治依据。 2、可判断病位和疾病的预后转归清·陶憺庵在《伤寒源流》卷三·渴总论[2]中论述口渴时认为:“伤寒渴者,邪传里也。邪在表则不渴,三阳虽有渴,不如三阴之甚。故太阴腹满嗌干,少阴口燥舌干而渴,厥阴则消渴。盖初传则热微而渴微,传甚则热甚而渴甚也。”指出了疾病过程中各个时期口渴的特点。 《伤寒论》71条和条的“渴欲饮水”明确了太阳病口渴并不太渴的特征。96条的“或渴”指出渴为少阳病只有热伤津液时才会出现的或然证。26条“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97条亦点明“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条更是明确指出“病人不恶寒而渴者,化转属阳明也”。辨别出病由太阳、少阳传入阳明的特点。 《伤寒论》条“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又在条中曰:“自利而渴者,属少阴”。用自利不渴与渴辨别病属太阴或少阴,清·陶憺庵《伤寒源流》卷二[2]中注解到:“若腹满咽干,手足自温,发黄者,为传经之邪,属热;若自利不渴,或呕吐,腹常痛者,为直中太阴之邪,属寒;从为太阴寒热之辨。” 《伤寒论》条“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指出下利与口渴等症并见,少阴病阴虚水热互结、津不上承的表现,亦是少阴病邪从热化之候。条“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论述了邪入厥阴,相火郁而上炎则为上热,火不下行,肾失温煦而下寒,形成上热下寒的寒热错杂证。 《伤寒论》41条(如前述)因外有表邪、内停水饮,虽发热而不渴;服小青龙汤后而渴者,是寒邪外解、饮邪内行、其病向愈之兆,因发汗后,温解之余,一时上焦津液尚少,故见渴象。71条“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本条也是汗后外邪虽解,但汗多伤津,胃津不足而口渴,因而予少量饮水后,胃得滋润,津液恢复,则诸证自除。条“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本条是厥阴虚寒证阳气乍复之征,胃津略有不足,所以少少饮之补充胃津即可向愈。条“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今自愈。”及条“下利,脉数而渴者,今自愈。”都说明轻微渴象反映了机体有良好的恢复能力,是邪去正复的表现。 四、《伤寒论》口渴方的临床运用 “口渴”做为临床中易被诊查的症状,应该受到广大临床医师的重视。《伤寒论》对口渴的辨治,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思路。有许多医家在继承《伤寒论》精神的前提下有了新的发展,先就一些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1、静氏等[3]用五苓散治疗中风后急性尿潴留,中风患者大脑功能受损则神经机能失调,导致急性尿潴留,中医认为是气化不及州都则膀胱不利,水道不通,水湿内停,故以“通利水道”为治疗大法,用五苓散化气行水健脾治之。冷氏[4]用加味五苓散治疗梅尼埃病,梅尼埃病的病理变化是膜迷路积水,一般采用扩血管和利尿等治法。中医认为其病机为脾胃虚弱,中阳不足,水湿内停,症见突发眩晕、耳鸣、听力减退、噁心呕吐,可伴有口渴。用五苓散温阳化气利水,佐以健脾降逆祛痰之品,收到了良好的疗效。 2、李氏[5]用白虎加人参汤治疗顽固性发热取得较好疗效,大部分病人接受过西药抗炎等的治疗而效果欠佳,症见发热、口干烦渴、饮水不解、汗出或无汗、肢倦乏力、食欲不振、面色恍白、舌质干红、苔少或腐燥、脉虚数,认为顽固性发热大多气阴两伤,脾胃呆滞,治疗时应顾护津液,以白虎加人参汤泻胃热生津液。屈氏[6]用加味白虎汤治疗经西药抗生素、抗病毒、激素及解热药治疗后不效的高热患者,症状除高热外,多伴有口干乏力、口干纳差、口干饮多、口干咽燥痛等,中医诊断为热痹,湿热型泄泻,热盛伤津,气分热盛等。用白虎汤加味清热通络,清热生津,胜湿止泻,清热养阴生津,收到良好的疗效。 3、岳氏[7]在临床中以口苦咽干、目眩、寒热往来为使用小柴胡汤的主症,通过加味广泛地运用于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发热,肝炎、胆囊炎、胰腺炎、突聋(中医称暴聋),妇科痛经和月经不调,呕吐,水肿,糖尿病,肝脾肿大等病症。刘渡舟教授[16]从“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悟而得之“小柴胡汤,少阳病主方也。少阳诸证,以口苦为第一证。《内经》曰‘火之味苦’。然它经之火,甚少口苦,唯肝胆有火,则多见口苦。故口苦反映少阳邪热有现实意义。‘但见一证’当以口苦为先。” 4、刘渡舟教授[8]在运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肝炎久治不愈者时认为:一般肝炎患者最初辨证为肝胆湿热,一段时间后由于肝病及脾导致脾气受伤,这时患者若继续服用苦寒药物或恣食生冷,则容易造成脾胃虚寒,而见腹胀,恶食生冷,大便溏,疲惫不堪,肝区疼痛范围增大,曲胁及背。此时病已经向寒湿转化,隐隐可见水象,故见病家面色萎黄,晦暗而发黑,舌胖苔白;临床少阳郁热未去,故有口苦、口渴、心烦、胁痛等症,胆热脾寒共见,治疗上必须肝脾同治。刘老用原方较少加减,仅在用量上调整。病人口渴、舌红阴伤明显时,加重天花粉的用量至12g,减轻柴胡用量。 5、廖氏[9]用小青龙汤加减配合西药治疗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疗效优于单用西药组的治疗。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病,但以寒冷湿偏重的冬春季多见,以咳嗽、喘促胸闷、咳痰为主要特征,病程长易复发,治疗上颇为棘手。小青龙汤以治疗水饮咳喘为主,宿痰、宿饮为阴邪,内伏胸腑,当用“温药和之”。 6、李氏[10]用大承气汤治疗急性尿潴留,症见:烦渴、头痛、无尿、小腹胀痛、大便干、舌红、苔黄腻、脉沉实。辨证属热结下焦者,治以峻下热结,少佐化瘀利尿。 7、魏氏[11]用白头翁汤加减治疗细菌性痢疾,中医辨证为疫毒型。症见腹痛剧烈,里急窘迫,痢下鲜紫脓血,腐臭难闻,壮热口渴,头痛烦躁,恶心呕吐,甚或昏迷痉厥,舌红绛,苔黄燥,脉滑数。方用:白头翁金银花白芍各30g秦皮地榆各15g黄连3g黄柏6g,神昏痉厥者加犀角、羚羊角,收到了良好疗效。 8、彭氏[12]用加味茵陈蒿汤治疗急性黄胆型肝炎收到了很好效果。主要病机为湿热蕴结,胆汁外溢肌肤,故以清热利湿退黄为治疗大法,方中重用茵陈清热利湿、退黄胆。 9、刘渡舟教授[13]认为猪苓汤是张仲景辨治水病的重要方剂,为后世开创了滋阴利水治法的先河。通过76例验案统计分析,探讨刘渡舟教授运用猪苓汤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76例验案中发病特点以中青年为多,男女无差别,多为慢性疾病;病因包括外感,内伤两大类,其中以感受湿热之邪、房劳及过食肥甘为多;其病机特点是阴虚水热互结,且以少阴阴虚为关键。使用猪苓汤的症状特点为小便不利、渴欲饮水、心烦不寐、尿血、腰酸痛、浮肿;舌象以舌质红绛,苔白水滑为主,脉以沉、弦为多。本方主要用于热淋,血淋,水肿,腰痛,癃闭等下焦病证。 10、华氏[14]报道针刺期门治愈胆道蛔虫症1例。症见右上腹阵发性绞痛4h,伴恶心呕吐,剧痛时汗出肢冷,辗转不安,痛止如常人。西医诊断为胆道蛔虫症,给予补液、解痉、抗感染治疗3天无效。患者呈痛苦病容,面色苍白,遍体冷汗,四肢厥冷,巩膜无黄染,舌干苔黄,脉细滑数,腹部平坦,右上腹拒按触痛。遂给予针刺右侧期门,进针0.8寸,得气后轻捻约3min,腹痛顿消,留针2h。留针期间未出现腹痛,出针后30min又腹痛如前,再行针刺期门穴如上法,腹痛又止,继续留针6h,疼痛未再发作。 11、大陷胸汤[15]由大黄、芒硝、甘遂组成,为峻下逐水剂,适用于水饮与邪热互结于胸腑之间的结胸热实证。症见从心下至少腹硬满而痛不可近,日晡小有潮热,心中懊恼,短气烦躁,口中燥渴,大便秘结,舌上干燥,脉沉紧有力。近代多用于肝硬化腹水、肝脓疡;合大承气汤治疗胆囊炎、胆石症;加败酱草、鱼腥草、柴胡治疗胸膜炎、胸腔积液伴发热等。 12、文蛤散赵川德《金匱方衍义》云:“其味咸凉,咸本于水,则可益水,其性润下,润下则可行水,合成凉润下,则是可退火治热,证之渴饮不止,由肾水衰少,不能制盛火之炎燥而渴,今益水治火,一味两得之。”临床运用嫌其力薄,故合三才汤(天冬、生地、人参)助之治疗肾阴亏损,虚火内燔,症见消渴、多尿、腰酸腿软、头晕耳鸣、失眠多梦、舌红苔少、脉细数等。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伤寒论》中口渴作为疾病的一个症状是有非常重要的辅助诊断的价值,其中为我们提供的方法和治疗手段很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口渴是临床中一个简便易行的用于诊断的症状,我们领会《伤寒论》中有关口渴病机,治则和方药的精神,对实际的临床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它有助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对口渴病机的分析,了解疾病的整体病机,通过证治口渴的方药的运用,帮助我们提高中医药临床中药物配伍化裁的能力。我们知道《伤寒论》以其对疾病病机概括简明,用药精当而著称,它为我们提供的关于口渴的四大病机和方药也同样要约不繁。在临床中针对一些病机复杂的疾病,可以从其口渴出现与否、口渴症状的程度以及治疗后口渴症状的变化来判断我们的辨证论治是否正确、证治中药物的选用配伍是否恰当以及疾病的病势和预后转归等情况。当前制约我们中医药临床的主要是对疾病病机的正确分析和认识,治疗中的选方用药。《伤寒论》所呈现的有关口渴的证治,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捷径,对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有着深远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章碧明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rwdbaog.com/fkdcb/2916.html
- 上一篇文章: 耳鸣的常见病因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